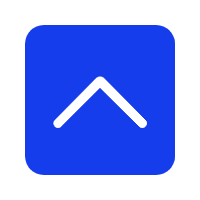战后的前50年,世界大格局无疑是美苏两极世界的建构与解构。后50年,我们预计,世界将逐步走向中美关系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虽云多极但向G2倾斜”的时代。而现在正处于这一时代的前半段,是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积累过程中逐步走向中线临界点的时期。虽然大趋势难以逆转,但这一时期无疑容易出现重要变数,因而是一个相关各方特别是有战略性重大利益关切的主要国家加大博弈力度的高度风险期。
因为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趋势,所以即便从国家利益比重的角度,对这一趋势最为敏感、反应最为激烈的,以国家而论,是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和紧随中国之后的日本。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世界按照自己的既定轨道前行,中美日关系聚焦于这个轨道的“切点”上:美、日上下其手,力图使中国行进在下切圆的轨道。因为常识告诉他们,一旦越过中线成为上切圆,惯性的作用即意味着要多付出的代价。而接近“中线”的上下切点,离心率都非常高,很容易失控,象征着这是一个高风险甚或高危期。
而当下预示这一高危期的象征,可谓集中体现在“安倍风险”上。所谓“安倍风险”,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蓄意推高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引发危机的风险,企图最大限度地借此激发国内的民粹主义,实现扩军修宪的政治军事目标;同时,“安倍风险”也包括日本拉战略东移的美国下水,推高中美在东亚直接对抗的风险,以求渔翁之利。
“安倍风险”的形成原因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安倍风险”亦如此。
冷战后日本的“三个神话”相继破灭。首先,战后日本最引以为荣的“经济神话”破灭,其后长达20 年也没有恢复元气;其次,“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的“超稳定政治神话”终结,代之以“十年十相”的政局乱像;第三,以“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东北大震灾引发的核电站事故为标志的战后“社会安全神话”被打破。
与上述“安倍风险”形成的国内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在野党、执政联盟包括自民党内派系之间,因为选举政治的原因,它们对安倍的制约大大弱化,这也是“安倍风险”不断得以加大的内在要素之一。
此外,安倍本人信奉的以岸信介为范本的极端保守、反动的政治理念,无疑是“安倍风险”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加之“梅开二度”对安倍来说意味着是最后的机会,所以“安倍风险”系数非常大,具有执著性的同时,也带有“孤注一掷”的冒险性和疯狂性特征。其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即为表现之一。
2013年, 地缘政治中海洋权益的效应也愈发凸显。日本是一个战略资源极度匮乏的发达国家,在陆地资源几乎开发殆尽的情形下,当代日本战略家高坂正尧指出,日本除了向海洋要资源、图生存之外,别无出路。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之后,日本借机正式确立了“海洋立国”的国策,大力推进包括将冲之鸟礁改造成“岛”等扩展“蓝色国土”的海洋战略。近年,中国逐步确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这本来是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并没有以此威胁日本的主观意图。但安倍处心积虑,以地缘政治的心理效应,以及作为岛国日本的国民因为资源、海上运输线的先天不足和脆弱性而形成的对海洋权益的敏感性,利用钓鱼岛主权争端宣扬中国的“物理性威胁”,放出“安倍军事学”的“安保三支箭”,就容易具有煽动性和欺骗性。
另一方面, 尽管美国重返东亚,“再平衡” 的选项很多, 但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其自身,还是对其盟国,在海洋权益方面制衡中国是其首选。对此不失时机地加以利用,不言而喻也是形成“安倍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
“安倍风险”的四大挑战
首先,“安倍风险”将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和平崛起构成重大挑战。
这表现在三个层面:在双边关系上,因为任期内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所以为达此目地,他必然会蓄意分阶段、有步骤地不断利用钓鱼岛等挑起事端,中日关系也就因而难有宁日。特别是严峻对峙下的东海海、空域发生其蓄意为之、或擦枪走火的风险,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不能排除发生局部军事冲突的可能。在地区层面,今年安倍将在去年放出“安保三枝箭”的基础上,实质性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安倍将迅速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越南等进行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军事合作,给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制造麻烦。在全球层面,安倍可以更放手地要求欧美在武器出口、高科技转让等方面对中国的限制,在世界军售等领域杯葛中国。
不言而喻, 在所有三个层面中,日美同盟都起支撑作用。特别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日美同盟的内涵,包括军事合作的区域范围、一体化程度等将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安倍上台后还一直热衷于在所谓地球仪外交中搞“2﹢
其次,在道德制高点上将带来全方位挑战。由于历史原因和自身特点,战后日本外交实践中向以经济为支撑,但安倍无论是在第一个任期,还是“梅开二度”,都高调祭出“价值观外交”,倾力打造“价值联盟”,意图从软硬两方面包抄中国。
再次,安倍风险还体现为外交上充当围堵中国领头羊的高度自觉意识。无论是在地区层面的遍访东南亚,还是在世界范围都有所表现。
安倍上台以后,一是一反战后日本外交一向低调的传统,表现异常活跃;二是针对性非常强;三是肆无忌惮———几乎在所有访问国都公开指责诋毁中国。他在精心编织对华包围网络时,公开宣称要成为制衡中国的“领导者”,做围堵中国的领头羊的意识可以说高度自觉。
最后,“安倍风险”还存在着“综合安全保障”方面的挑战。“2﹢2”之外,安倍还热衷于以经济援助捆绑安保以制衡中国,这特别表现在他的东南亚和非洲外交上。结合上述三个方面,仅就东南亚而言,“安倍风险”已经给中国造成重大挑战。即中国要付出更多的外交努力和资源,才能对冲。而在即将启动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也会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局面。
管控“安倍风险”
对于中国来说,管控“安倍风险”可依以下三策:
一是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如果中美关系能维持相对正常状态,日本就不会走得太远,“安倍风险”亦在可以管控范围。一方面因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对手,利用日本制衡中国将成为其长期的地缘政治战略取向,另一方面中美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把握好相对的两个方面的平衡点,同时也是制约“安倍风险”的关键点。此外,日美之间在现实利益和对二战成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体系。
应该说, 这些基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建立起来的被“神话”的认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发酵。问题在于,一方面,所谓的“西进”战略更多是从事非欧亚地区研究的学者的一项个人战略设想。另一方面,历史地看,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海权和陆权力量博弈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大陆性权力获胜的记录, 与中国西部大周边的边缘性权力相结合, 就足以确保中国与美国挟TPP、TTIP等形成中的国际机制抗衡吗?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外无一例外地低收入国家,足以充当中国剩余产能和过剩产品的转移市场吗?显然答案都是否定的这些有强烈偏差的认知反映出的正是外部世界, 首先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正在日益改变世界这一事实的强烈忧虑、怀疑和防范,而对中国周边外交整体, 尤其是其欧亚环节中饱含的合作性、包容性、公共性视而不见,对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以及地区和国际合作机制保持协调、合作乃至共振的良好意愿视而不见。这种有意识地忽略中国“不谋求欧亚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 的基本立场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欧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好,中国-中亚“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也好,都不能简单地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予以解释。它不是中国致力于推进封闭的大陆亚洲体系的新信号,更不是借此与其他国家相抗衡的努力, 而是将开放的海洋体系和相对封闭的大陆体系予以整合的一种尝试。这一点从海陆丝绸之路并举的倡议中可见一斑。换言之,中国将继续甚至进一步强化过往三十余年对海洋亚太(首要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此同时,中国的新欧亚战略绝不意味着试图建立任何替代性的、排他性的大陆亚洲体系。相反,一种新的局面可能正在出现,即中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贯通之势呈现在新世界秩序中:东向南向的海洋开放与中国内部从东至西的广袤地带的国内一体化以及以俄罗斯、中亚为支点并继续向西开放的跨海陆整合体系。这样一来,中亚国家参与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体化进程,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后苏联空间, 而是从欧盟一直到东亚这样一个广泛的欧亚空间宏大一体化进程中一部分, 从而与中国建立起更为休戚相关的紧密关联。进一步讲,中国的发展就不仅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也和发达世界的发展内在地融合在一起。基于此,中国的未来将以中国加入这个宏大的海陆一体化体系所定义,同时未来的国际秩序和地区格局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由这一进程所定义。
“丝绸之路经济带” 议程的优势
在我看来,2013年中国在欧亚地区的外交和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为标志的议程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
第一,中国的方案将整合重心放在全面经济合作上, 以立足中亚、超出中亚的宏大战略视野,整合欧亚大陆,尤其是以中国和欧盟为两端的综合力量,统筹中亚国家及俄罗斯,统筹经济和社会,统筹交通和能源等地区公共产品,不包含其他全球和地区大国和中等国家的一体化战略中的政治、价值导向内容。
第二, 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已经承诺的具体资金投入也使得这一方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相对而言,美国“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较1999年和2006年的两个丝绸之路法案更为仓促,其冲击-反应的逻辑很明显,即首先为美自阿富汗撤军后的后2014年代的欧亚提供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话语体系。美国最大的困境可能在于自身国力处于下降期,寄希望于企业落实相关投资项目但它们却对该地区投资的风险高度忧虑而望而却步。同时, 由于美国推进新丝绸之路计划过程中强烈的排他性, 地区国家对此言辞积极而行动消极。
第三,中国与欧亚地区国家在苏联解体以来积累的合作成果, 尤其是制度安排为这种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和俄罗斯以及中亚地区相关国家在后苏联时期围绕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谈判机制,经过边境地区信任措施等予以强化,此后一步步转换为更广泛合作的“上海五国”机制,最终经由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 已经将中国对开展与欧亚国家的密切合作及在此过程中保持开放性、平等性、共享性的政治承诺从话语变为一种规范。新建成的群体性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也将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第四, 全球化在欧亚地区的疏漏网点正在被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网络填补,新的合作方案并非从零做起,而是将之制度化,实施难度相对较低。以渝新欧铁路项目为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等国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成功的国际互联互通合作,无疑加大了跨欧亚大陆一体化并将之与亚太海洋合作体系勾连的吸引力。
总之, 未来的国际关系史和外交思想史学者在书写2013年中国周边外交中的欧亚篇章时,一定会注意到其中的大转折和新起点等多重表征。在2013年这个特定的时空结构中,中国周边外交的欧亚时刻正式形成,并可能极大地影响中国的大国成长之路。我认为,相较于其他大国的欧亚地区整合战略,尤其是与俄美欧相比,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仍停留于构想的初期阶段,本身的内容尚有不明晰之处, 这也加大了外界的观望和疑虑姿态。因此,当下最关键和最迫切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将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内的诸多周边外交新设想从话语变成实施细则,进而转化为一种被所有参与方都能接受的规范。在此过程中, 一切不改变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以来的固有经验而将之生搬硬套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欧亚新外交议程中的做法都有可能产生走偏效应。在根本上,中国有必要从沟通海陆丝绸之路的战略高度将对欧亚国家的合作变为调整对外思维的重要舞台和走向成熟大国的演习场。只有当中国以一种基于世界主义战略视野甘愿担当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服务者而不仅仅满足于将本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输往欧亚大陆之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才会在真正意义上获得成功,中国的欧亚新战略才会真正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国际起点。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历史契机。